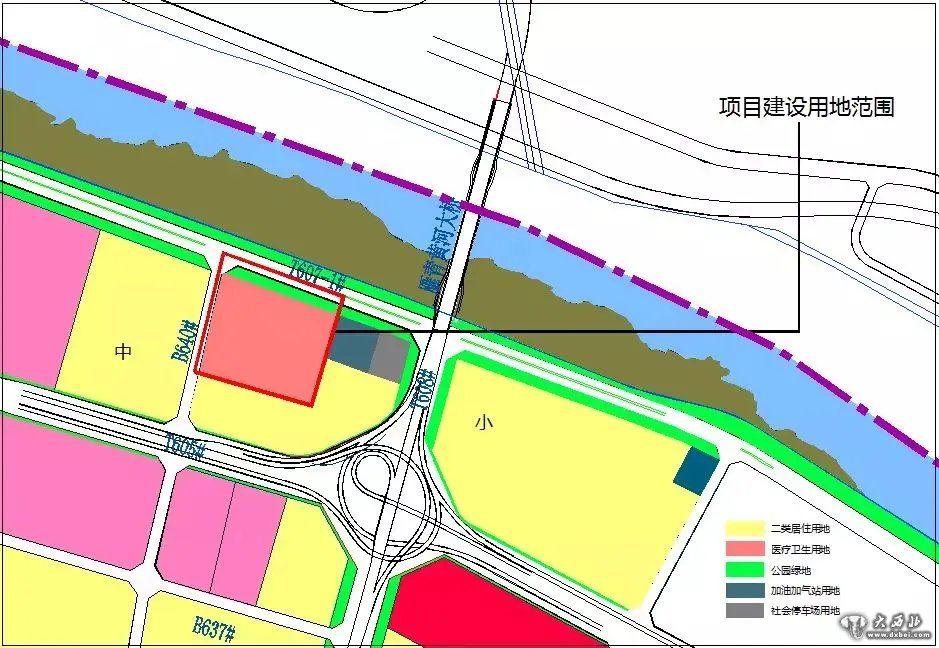9月6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有准入条件。家长须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且是常住人口;学生本人要在该地上学;当地城市需要这个行业群体。(《新京报》9月7日)
先不说“稳定”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就只“当地城市需要这个行业群体”一条,在地方的自主定义中,就可以将异地高考的大门封死一大半。问题是,谁最渴望异地高考这个“良政”的眷顾?笼统地说,是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然而,那些“当地城市需要的这个行业群体”、“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的常住人口”,多数可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户籍,即使没有获得户籍,他们中的多数估计也有能力选择让孩子出国的途径来接受优质教育;真正的渴望者,广大外来普通务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农民工,恐怕又只能望“异地高考”而兴叹了。
异地高考事关教育公平,无条件地放开,当然也不公平,甚至会对教育公平造成伤害,所以设置一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的。然而,怎么设置异地高考的前提条件,背后则是既得利益与增长利益的博弈。抛开所谓对城市承载能力的考量,真正的核心利益是招生资源的分配,是占用户籍地的指标,还是占用高考所在地的指标?按照常理,在哪里创造和贡献资源,就应该在哪里获得分配和享用资源的权利。这样的逻辑,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流动人口大城市,需要面对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压力就会更大,将来设置的条件也将更加苛刻。
从理论上说,教育公平应该考虑的对象是接受教育的孩子,让所有的孩子有一个公平教育的起点和竞争机会;而不是孩子的家长,将异地高考前提条件聚集在家长身上,就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拼爹”游戏,依然在加深社会阶层的固化。从孩子的角度说,只要接受的高考前教育相同,就应该获得同等的高考机会,异地高考只需要防止“高考移民”的投机即可。而背后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不均衡的现实、户籍制度的藩篱等,既不是家长能够左右的,更不是孩子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在政府,难题只能由政府来破解。
公平,一个是救济意义上的公平,即,打破原来的利益格局,重新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另一个就是发展意义上的公平,即,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特权,而是以其为参考标准,通过发展使权益获取普遍达到特权化的水平。目前,在北京、上海能上北大、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上海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公平的问题,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正因为如此,才提出了异地高考的命题。如何顺利实现救济意义上的公平,专家建议可行的路线,一是按照考生数量制定招生计划,二是实行名校联考的统招制度。
在目前的现实下,通过对家长设置苛刻的前提条件的异地高考,本质上并不会产生多大教育公平的效果,而只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范围稍稍放宽了一点而已,这与《教育法》“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的规定仍有很大的差距。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母,如果农民工子弟依然因为父母是农民工而无法获得异地高考的权利,所谓的公平又该从何谈起呢?
如果按照目前的前提条件设置异地高考的准入,对广大普通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无疑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实际上,异地高考本身就不是解决教育公平的根本之道,而只是一种补救性措施,但如果我们在这种补救性措施上都看不到真正公平的决心,我们还能期望真正的教育公平吗?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