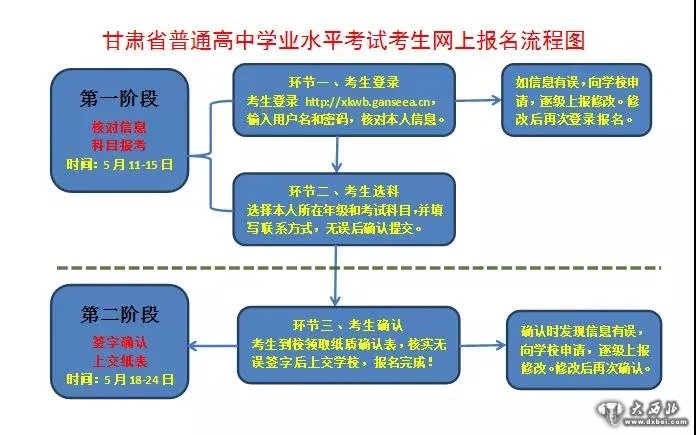2019年10月25日下午,因为一个自称“老太婆”的老人的到来,金城的午后,变得异样温暖。
她,就是樊锦诗。
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樊锦诗的名字像敦煌一样,更加深入地走进全国人民心中,走向海外世界。
2018年12月18日,樊锦诗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樊锦诗,是全国唯一一位“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10月4日,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在香港举行颁奖典礼,樊锦诗获“正能量奖”。值得一提的是,“吕志和奖”正能量奖,不但要求获奖者具备世界性的成就和贡献,还特别注重对获奖者作为精神道德榜样的考量,强调鼓舞人们在艰辛和逆境中追求建设性的改变,在推动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中的无私奉献。
10月21日,由樊锦诗口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撰写、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在北京大学发布,与广大读者见面。
……
这是一位81岁老人最近的行程,闪烁的光芒,足以慰平生,也足以照亮更多人。
“我也是南方人”
“我也是南方人,很想回去。”没有刻意的表白,在当天举办的樊锦诗获国家荣誉称号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出版座谈会上,樊锦诗坦言,刚到敦煌时真的想走,因为一个搞科研的地方条件怎么能那么差。
可又不太想走,因为莫高窟确实太美了。
走和不走,樊锦诗都不太坚定。
“其实,我这个人比较笨,也比较傻。”樊锦诗说,自己摇摆不定,但组织让自己待在敦煌,自己就待在敦煌。
“他们怎么能待下来,我真是奇怪。”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把敦煌当成自己的家,把敦煌融进自己的血脉里,把敦煌变成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太了不起了”,樊锦诗被深深感染。
时间长了,樊锦诗对敦煌的感情越来越深,也逐渐明白、理解前辈为何能默默无闻,在大漠深处,献了青春献生命,献了生命献子孙。因为,敦煌的价值之高无法估计,敦煌的资源之多用之不尽、取之不竭,“莫高窟这座文化遗产实在非同小可。”
“我的命运好像就在敦煌。”既然待着,就要做点事,就要把前辈未竟的事业做好,樊锦诗回忆道。
1944年,惊艳于中国艺术之美,已在巴黎颇负盛名的东方之子、画家常书鸿从法国巴黎来到大漠戈壁,白手起家开始了敦煌研究院的创业史。
到1962年,樊锦诗到敦煌时,已过去了18年。
“常先生去敦煌的时候,完全是一片废墟啊。”樊锦诗说,但在18年时间里,前辈们做了大量修复、保护、研究、测量、临摹等工作,为后来的敦煌研究院开展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必须做好接力,“否则,对不起前辈。”
“我真没想到”
1938年出生的樊锦诗,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全过程,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她没想到,自己会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更没想到能荣获国家荣誉称号。
“我也没想到,我真不知道哦!”樊锦诗回忆道。
有人对她说,你就穿成这样去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啊?“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啊!”质朴无华、甚而有些童言式的语言引来一片会心的笑声。
“当时,有点‘开小差’,脑海里马上想到了前辈和同事。”樊锦诗坦言,“改革先锋”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荣光属于无数先辈和莫高窟人。敦煌研究院能有今天,功在祖先千百年来多元性、持续性“接力”,留给我们一座独一无二的文化宝库;功在一代又一代莫高人坚守大漠、无私奉献的艰苦奋斗。
“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时,特别穿了一件丝绒的棉衣。”回忆起9月29日那一天,樊锦诗像个孩子一样,言语里充满童真与兴奋。
“第一次去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印象深刻。”樊锦诗还记得,因为自己的姓氏笔画数最多,所以排在最后面,习近平总书记站了有半个多小时。
“我们又见面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樊锦诗颁授勋章时说的一句话。樊锦诗很自豪。
之后,樊锦诗又受邀与同获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其他人,一同到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大典,“心里更加不平静”,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国家简直把我们当成‘宝’了。”又看看周边张富清、李延年等人,樊锦诗“感觉很惭愧”,“这些老英雄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从‘改革先锋’到国家荣誉称号,荣誉越来越高,我不过是万千文物工作者的一份子。”樊锦诗忐忑,却也欣慰。这么多年,樊锦诗“对文物两个字比樊锦诗三个字更敏感,也有更多想法”,“这些奖要拿给甘肃人民和甘肃的领导看看。”
“我心归处是敦煌”
“世界太小了。”樊锦诗又接着讲《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诞生史”。
以往,有不少记者采访樊锦诗,写关于她的报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为她写传记。
樊锦诗总是不假思索,一一拒绝,“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
后来,同行、同事、朋友都劝樊锦诗写一部回忆录,“写你,也写敦煌啊”,说得多了,樊锦诗开始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也对,那就写吧。”樊锦诗明白,自己在敦煌工作60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正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60年,“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也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
也是天意。
2014年,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到莫高窟考察,樊锦诗和艺术学院的教授顾春芳一见如故。
“她多才多艺,知识面很广,眼界也很开阔,很聊得来。”樊锦诗对顾春芳不吝溢美之词。
从敦煌回北京,顾春芳就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关于莫高窟的,一首是关于月牙泉的。
樊锦诗看着喜欢。
“那就再来啊。”没多久,北京大学的这几位教授又说“还想再去敦煌看看”,樊锦诗热情地邀请了他们,“莫高窟也有个宾馆,虽然不如北京的,但还凑合,住下来慢慢看。”
谁知他们来了,说还有一个任务,“给你作记录。”
“行。”这次,樊锦诗二话没说,答应了。或许是与自己毕业于北京大学有关,“相信他们的学问。”
樊锦诗和顾春芳的访谈持续了十多天。因为信任,樊锦诗特别放松,敞开心扉、毫无保留,问什么说什么。
“不能光说敦煌研究院的事啊,也说说你自己。”顾春芳也会提“意见”。
有一次,樊锦诗到顾春芳的房间,发现偌大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敦煌历史、敦煌艺术、藏经洞文物、壁画保护等方面的书籍,樊锦诗情不自禁地说:“顾老师,你太厉害了!”
樊锦诗知道,顾春芳并非考古、文物专业,也不是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写这本书,也着实为难。加上北京、敦煌相距遥远,见面不易,就尽量多提供一些材料给顾春芳。
“看到初稿时,大大超出我最初的想象。”樊锦诗觉得顾春芳很辛苦,又非专业出身,“我有责任配合她做好校对工作,尤其是把事实搞清楚。”
或许,好事多磨。2016年,此书完稿。2017年,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病重;2018年,顾春芳的父亲病重……
直到今年3月,樊锦诗又重拾此书,到7月初完成校对,又和顾春芳一起梳理框架。
从“人生的不确定性”“神圣的大学”“敦煌是我的宿命”“千年莫高窟”,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的女儿”,再到“保护就是和时间赛跑”“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传》分13个篇章,以时间为序,将樊锦诗和樊锦诗心心念念的敦煌娓娓道来,封面上写着“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反正您的心就在敦煌,书名就用‘我心归处是敦煌’吧。”自称“我是敦煌的‘老太婆’”的樊锦诗,对顾春芳的这个提议回答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