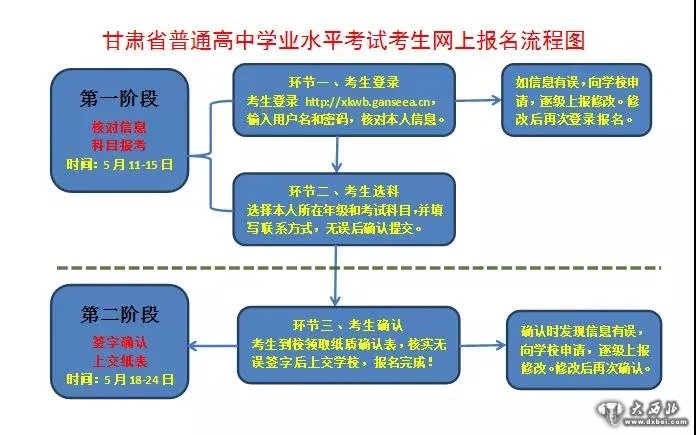一对68岁的双胞胎兄弟,用48年种了一片山林,然后日子变了……
喝茶、赏菊、住园林
10月的一天,秋意已浓。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许堡社,68岁的许志强午饭后小憩了一会,起身走到院子中间的亭子里坐下,和双胞胎哥哥许志刚在石桌上点起木炭,准备煮罐罐茶。
从空中俯瞰,老许兄弟家被几百亩青松翠柏包裹,一座白色亭子点缀其间。亭子后是一座木结构大房子,房檐上有木雕的龙兽。占地两亩多的院子一入门,一条干净的砖铺小甬道两边,两排松树苍然挺立。由甬道进入院子,别有天地:带着月亮门的矮墙隔出新旧两个院落,翠竹、松树、柏树高大浓翠,桃树、海棠、梨树一挨春天便繁花满树。
罐罐茶是西北人喜爱的一种茶道,两寸高的圆筒形小铁壶里放上茶叶和水,煨在架了木炭的火盆上,煮上半天也就够喝一口。年轻人大多不爱喝罐罐茶,耐不下心等,但却是老许兄弟的酷爱。老兄弟俩说喝罐罐茶不是为了品茶,更不是为了解渴,而是等待茶沸的过程,这种“消磨”的滋味美好得无法言说。
趁着煮茶,许志强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油饼,抹上一层自家养的土蜂酿的蜜,小小咬了一口,随后拿起一根老树根和哥哥雕了起来。可能是有些乏了,在烟雾缭绕间,兄弟俩不知不觉眯了过去。一觉醒来,微雨湿了地面,但什么时候下的,又是什么时候住的,一概不知。
许志强和哥哥起身走下亭子,穿过种着侧柏和云杉的小道通往后山。细雨飘落的天气,老哥俩最爱去山林里看菊花。在后山,三头菊、四头菊、五头菊,仍在开放。菊花都是野菊,天生天长,兄弟俩摸摸这朵,又摸摸那朵。“美!比公园里的美!”老哥俩笑眯眯对视着,脸上的褶子一起从嘴角慢慢向眼角集中过去,但眼睛却愈发明亮地像个孩子。
48年“种”出来的家
在剁开一粒土、两半都喊渴的黄土高原上,能坐拥一片满沟满屲的绿和一座山景园林的庭院,是两兄弟用了48年的时间一棵树一棵树“种”出来的。
黄土高原过去遍地是荒山秃岭。许志强兄弟的家乡也一样。不下雨便罢,一下便成水灾。在老人的记忆里,房前屋后到处是水从山上冲下来形成的“窟圈”。一下大雨,家紧挨着的土崖就会被雨水冲陷,“窟圈”越冲越大,山水卷着泥汤漫进院子,雨过天晴只留下一层没膝的烂泥。1968年的一场大雨,许志强媳妇担水时滑进“窟圈”,差点没命。
“再这样下去,要不上十几年,不但先人留下的庄子会被冲走,就是命随时也可能被窟圈要了。”许志强当时从电影上看到栽树能防止水土流失,便暗暗下了一个决心:用树根把这片山上的黄土“串”住!
黄土高原植被稀疏,干旱加上土质涵不住养分,当地老话说,种活一棵树比养大一个孩子都费劲。老许兄弟头一年种下去的几亩树苗遇上干旱,全军覆没。
几年过去,境况没有改变,栽上的树苗要么旱死,要么被水冲走。时间长了,兄弟俩慢慢发现,树苗之所以不耐旱、易冲走,是因为栽到了山坡上。他们把被水连根拔起的树摆成一个大格子的形状,淤积起一片地,再在上面栽树,成了!
种树要花钱,为了这事,许志强兄弟俩没少和各自的媳妇“耍心眼”。包产到户那年,许志强家里卖了一匹马驹得了700元,媳妇让他存起来准备盖房用,谁知老许掉头就从60公里外的林业站拉了三拖拉机树苗回家。家里人都憋着气没人愿意跟他种,许志强就自己种。碰巧天下雨,700颗树全活了。林业站的老站长得知这消息专门跑来,看着使劲抽枝拔叶的树苗说“以后站里的苗子便宜给你”。
种的多了,兄弟俩发现,在黄土高原上种树要“抱团取暖”:树越稠密,成活率越高。为了把山林种成片,包产到户后,兄弟俩一狠心,把十亩良田换成30亩荒坡。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山沟,许志强和哥哥倒腾粮食、贩卖牛羊和农副产品,一天能挣5元钱,而当时一个技术工一天工资才5角钱。村里的人都说,兄弟俩是聪明人。钱挣了不少,但却都“种”在了山上。因为种树,家里的生活一度很艰难,但许志强仍“死不悔改”。老伴养了一些鸡补贴家用,有一次让他去卖鸡给孩子做件衣服,许志强卖完鸡转头就买了30棵树苗。
黄土地上的小江南
老了老了,对树和绿色的爱却愈老弥坚。前几年许志强得了前列腺炎做了手术,医生说一年不能干活。育的苗子太多,许志强放不下,就做了一个草包垫在屁股底下,干完一点就抽着草包往前挪一下。
“陈芝麻烂谷子不说它了。”许志强拿起扁担,准备给过冬的苗子再上一遍水。下山的土路很陡,不到固定的地方放不下扁担。爬坡的时候,老许把前脚掌插进土里,全身重量压到脚上,另一条腿撑住地,用力一转,一个落脚点便形成了。老许说,山林里的路都是这样“修”成的。
沿路不时见到一些形状有些奇怪的树,记者问这是什么,老许说,这是芒果树,旁边是棕榈树、华山松、白皮松……
吃够了“黄色”满山的苦,老哥俩心底对绿色有一份偏执,种的树全是常绿树种。有句话说得对,如果坚持下去,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连南方的橘子树、佛手、无花果等兄弟俩也全种上了,一开始连林业站的技术人员都不看好,谁知在老兄弟手里养了一段时间,这些树竟然适应了这里的土质和环境,不但郁郁葱葱,还开花结果。
说着来到一个几天前下雨冲成的“水旋子”边上。水面离地面有一米多深,许志强先是用铁锹在岸边铲了几下,弄出来一个几十公分的斜坡,然后把铁锹深深踩了一脚,一只手扶住铁锹,借着往下的惯性溜了下去。蹲下后,手臂带着身子伸得长长的,才能够倒水。两个水桶舀满,许志强把担子挑在左肩上,先颠了一下,转过身,右手撑住铁锹,左脚踩住斜坡,身子一挺窜了上去,身子站直时,顺带又把铁锹拔了出来。
一桶水倒在树下,还没等流淌,便被土吸了进去。几个来回,许老背后便出现了汗迹。
“您这把年纪了,还这样干,辛苦吗?”记者问。“不辛苦。电视上,年轻人亲来亲去,今天好明天又不好了,没有我跟这山亲。你种了树,对它好,它就不会不对你好。”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南京林业大学读书的孙女许童玲每次学校放假坐火车在定西下车后,感觉回到了黄土高原,满目苍凉,但车拐进家里那个山坳坳,许童玲感觉又回到了江南。“家里树特别多,和南方特别像”。
看上去是老人,心里却藏了个顽童
48年、400亩山林,许志强和哥哥每天就是这样爬高窜低。光阴流转,山林越来越绿,老哥俩却由一对壮小伙变成了花甲老人。但许童玲却说,大爷爷和爷爷一辈子爱树、种树,已经“天人合一”了,看上去是老人,心里却藏了个顽童。
“爷爷特别喜欢动物,我们不想让狗狗上床,爷爷就抱着狗睡觉。爷爷养了一笼子鸡,关在笼子里怕鸡闷,就每天在坡上放鸡。感觉爷爷和别人家老人不一样,别人都为了孩子,我爷爷想很远的事儿,比如跟我们说要爱环境。”
“爷爷爱唱戏,唱秦腔,拉二胡,让我们姐妹学秧歌,他给我们画脸。”
“大爷爷去集市,就是买花,最喜欢牡丹。”
“下雨了,蜜蜂翅膀湿了,爷爷把蜜蜂捂在手心里,把它捂热了,翅膀干了,才让它飞走。我们都害怕蜜蜂蜇人,但蜜蜂从没蛰过爷爷。”
“爷爷和马也有很深的感情,叫一声马就过来了。家里有一匹马老死了,我以为会卖给屠宰场,没想到爷爷把它埋了,埋在树林里面。”
许童玲说这些时,老许兄弟俩在一边笑眯眯地听着。一只小花狗跑过来,在许志强鞋子上舔了几口,蹭着裤脚卧了下来。
记者嘴里长了疮,许志刚从树上摘下一大把浅黄色的金银花,让泡水喝。又顺手揪了几根细长的绿色叶子,“这是川楝子,可以入药。”
“你知道吗,我两个爷爷除了种树,一个专攻绘画,一个专攻根雕,都是老有所成,远近闻名哩。”许童玲有点小得意地把记者拉到二老的“创作室”:迎面挂在墙上的是几幅工笔牡丹,有的含苞有的盛放,华贵又大气。中间放着一排古意盎然的“玄关架”,摆满雕好的根雕,“大鹏展翅”、“金猴献瑞”、“凤凰于飞”等动物题材的作品,取材自然,件件活灵活现;“老子出关”“三娘教子”“关公夜读”等人物题材的根雕则神形兼备、韵味久远。
“这是咋学的?”记者很吃惊,这些作品的水平怎么看也跟面前两个山洼洼里的老农八竿子打不着。许志强兄弟说,黄土高原十年九旱,但山也是通人性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时间长了便心平气和,干什么都学得快。
是啊,老人说得对,既居山野,便顺其自然,一座庭院也可装下整个人生,这也许就是大山对两位老人一生植树的回馈。
回程了,老哥俩赠送的菊花放在车上一路散发淡淡山野味道。车子翻过山顶时,从上面望下去,汪洋绿色中的一顶白色八角亭格外醒目。那两张一笑起来褶子就从嘴角慢慢向眼角集中过去的脸,和那像孩子一样明亮的眼睛,在记者脑海久久浮现……
(责任编辑:张云文)